1365 views

2017的元旦,邓文迪因为一张在微博上和21岁“小鲜肉”的合影而再次引爆话题,既有称赞她传奇女性、人生赢家的,也不乏说她靠出卖肉体获得金钱、败坏世道的。
1月11日,罗玉凤的文章《求祝福,求鼓励》(见文末原文转贴)刷爆朋友圈,同样褒贬不一。有人说凤姐聪明有才华,是“敢做梦,不认输”的草根代表;也有人批判她一路卖丑秀下限,通过抹黑国家留在美国,配不上“梦想”二字也不配得到鼓励。
邓文迪已跻身上流社会,上东区豪宅往来无白丁;凤姐也已身在美国,继续等待绿卡。两个女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,然而她们的叙述中又有诸多相似之处。
邓文迪在VOGUE的英文采访中,回忆自己的童年:“我成长在一个小镇,那里不通电,没有电话,没有电视,没有冰箱,没有热水。那儿的生活非常无聊,我没有玩具,也没有洋娃娃,什么都没有。”提到她在排球队和出国读书的经历,她说:“你并不知道自己很穷,因为这就是你长期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关注,你必须要很聪明。… 为了摆脱我贫穷且无聊的人生,我必须要申请到奖学金。”
罗玉凤也在文章里提到了自己家庭的贫困:“屋内昏暗无光。灶是用泥土和砖垒起来的,一口大铁锅里装满猪食…”说到自己去上海、去美国的原因,她说自己只是不愿意认命。
两个人都想要摆脱贫穷和庸常,都是个人野心大过眼前的现实条件,都通过社会主流所不认可的方式暴力成名、获利,都不在意大众的唾骂和眼光,都通过世俗认可的一些标准来达到了不同程度的“成功”。两个人的叙述中,都隐含着一条残酷的现实:若草根不成名,则苦难无意义。她们的贫穷和不甘心,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和同情,因为像她们这样家境的人太多了。
VOGUE采访里邓文迪没说出口的,罗玉凤在文章里替她说了。罗玉凤说她只是想成为“他们”,她觉得去了上海、去了美国、拿到绿卡,自己就可以麻雀飞上枝头赛凤凰;在她眼里,成功和阶级是几个简单粗暴的指标,一条条打勾划掉就可以跨越的鸿沟。然而罗玉凤也好,邓文迪也好,不管她们多么努力地往上爬,终究难以摆脱“城里人”或精英阶层眼中的异类形象,因为她们草根出身,带着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、一切皆可牺牲的狠劲儿,“吃相难看”,没有踏踏实实地努力;她们抛弃的令人害怕与厌恶,她们得到的令人羡慕与嫉妒。
与邓文迪不同的一点是,罗玉凤有着明显的相貌劣势,也正如此,她遭受的嘲笑和唾弃更加猛烈。踏踏实实在小镇努力一辈子的罗玉凤,可能永远达不到现在的她所拥有的名气与机会。她卖丑、炒作,在骂声中越战越火,遵守的正是这个时代人成为消费品的流通规则。所以我们不只看见了凤姐,还看见了“快手”视频里的二哥炸裤裆,山东小闯自虐吃东西,庞麦郎破音的歌唱,把自己PS成蛇精脸的刘梓晨,在各类真人秀中痛哭悲惨家事的选手们,以及揭露明星们过去艰辛经历的月经贴。
去年曾有一则帖子在微博上爆红,题目叫《看到她化妆后的照片,忍不住泪奔了》。一家摄影机构决定为那些“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走进摄影棚的女人”拍照,他们找了身为建筑工人、清洁工、摩托配件厂女工、超市销售员、裁缝的几位女性,一改她们平日不起眼的衣着,为她们化上精致的妆容、穿上美丽的服装,拍了几组时尚的照片。文章的结论是:如果条件允许,谁不是花容月貌?然而那些相片里被人们惊叹的优雅瞬间,并不是这些劳动女性平时的样貌,她们平日的素面朝天,仍要靠这千篇一律的打光和PS修缮,才可以被接受为“美丽优雅”。
而为了这些草根网红献上赞美、嫉妒、愤怒乃至唾骂的我们,既是这条消费品流水线上的验货员,也是消费者:他一无所有、不择手段,多么丑陋;她有了名气,背后肯定有故事,要学习;他已经这么火了,谁能想到他经历了这些?感动、鄙夷和钦佩、排斥和同情,都来得迅疾而廉价。
但故事只属于这场消费浪潮中的弄潮儿,那些还没有成名致富的人,是丑的、是笑话,不配说起自己的故事。在消费这些故事的过程里,我们终于从自己黯淡无光、饱受碾压的生活中,获得了一丝身为强者的优越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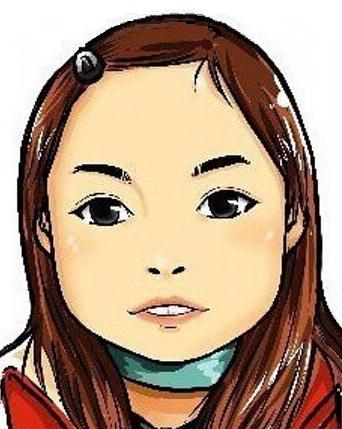
附:
不知道为什么,最近我脑子里总是想起我妈当年的这句话,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,她叫我认命,现在想想其实也是为我好,虽然我妈不晓得“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”这句话,但是生活的艰辛早就让她懂得这个道理。她让我认命,其实也是为我好。
从小,她对我确实也没什么期待,小的时候她只是希望我带好妹妹;长大一点,她只是希望我不要让家里为难,不要读高中去读师范;我能做一个乡村教师,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的工资,能寄点钱回家已经是满足了她对我所有的期望;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从奉节那所小学辞职去上海打工,更不能理解之后发生的事情,“她之前没有受过啥刺激,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”我妈当时是这么对记者说的。
其实我没有受什么刺激。

家里很穷,日子很苦,一家五口人只有7厘地,我恨过老天爷为什么让我家这么穷,但我从来没有怨过我妈,我继父没本事,相反,我很感激他们,即使这么困难,他们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供我读书,还记得我读綦师时,继父在綦江水泥厂上班。我每个月都会去他那里拿150元生活费,有一天我去找他,人家说你爸爸在里面倒铲煤。我进去看到爸爸了,他穿得很脏,推着个车,里面装满了渣滓,水泥厂空气很浑,噪音很大,爸爸出来给我拿生活费。这个场景时常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梦境里。
别人说如果一个人开始频繁的懊恼过去做的决定,开始想“如果当时我……那么现在也许……”就说明这个人开始老了;我发现我现在开始老了,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当时我不离开学校,我今天会怎么样;看到我当年那些教院的同学都变成晒儿党的时候,我也确实对当初的决定有过后悔。有时候一想到自己漂洋过海的到美国,这么久了,还是一个人,我也会情绪低落,也会很烦躁,甚至也会后悔,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因为是受了什么刺激。
可是每当我把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掰开了,揉碎了来想,我的那些决定真的不是因为我受过什么刺激,我只是不认命。
对,只是不愿意认命。
我从小生活的洋渡村,一墙之隔就是重庆钢铁公司綦江铁矿。国企职工子弟衣着打扮,言行举止与农村人完全不同,处处透着精致;和他们相比,我们这些洋渡村的人处处土里土气的,重钢的子弟们用“农村娃儿”来表达对我们的轻蔑;虽然他们看不起我们,但是我们,至少是我,却很想成为他们,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工人子弟长得就是比农村孩子漂亮,学习成绩比农村孩子好,家庭条件就是比农村孩子要富裕(只有这条,小时候的我猜对了。)只是我家很穷,没有办法给我买漂亮衣服,漂亮的文具,我只能认为如果我学习成绩好,爱读书,也许他们就会接纳我,我也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,后来的事实教育了我,我还是太天真了,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强烈的挫败感,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。
我读教院的时候,很幸运的结识了互联网,也学会了写诗,开始知道海子、顾诚、博尔赫斯,那个时候我很少和同学交往,主要是和论坛的诗友们交流,现代诗不仅是一场朦胧的美梦,也让我做了一场“我成了他们”的美梦;有一次重庆的诗友聚会,我也去参加,诗友们请我吃了顿肯德基,吃到一半的时候,诗友们告诉我,这顿她们请客,她们还有事,先走了。
“梦幻(我当时的笔名),你慢慢吃哈,我们先走了。”
我要说,那些诗友是好人,她们看出了我的窘困(那时我在教院勤工俭学,一个月能挣150)没有让我AA,我为了这次聚会带了100块钱;只是现实又一次告诉了我,会写诗并不意味着“我能成为他们”,当然也不意味着我就有男朋友。这种强烈的挫败感一直伴随着我到奉节的学校工作。因受这件事的刺激,那个时候的我还小小的愤青了一下,曾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,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体面的城里人。
奉节的学校其实也没什么不好,是,那个地方经济很差,辣条都能上桌当一个菜,但是比起我家来说,其实也并没有差到哪里去。工资收入其实还算可以,我只是不甘心想一辈子就这样,我只是很想成为“他们”。(“罗玉凤的妈妈正在一个破旧的小窝棚内煮饭。屋内昏暗无光。灶是用泥土和砖垒起来的,一口大铁锅里装满猪食,另一边架着的一只锑锅,煮着清水白菜,没有丁点油水。灶面上卧着一只肮脏的老猫……”这是后来我征婚后记者到我家采访时的素描,大家感受一下。)
最后,我做出了辞职去上海的决定,为什么选择上海? 只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。“都认为我就这样了,那我就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去,让你们承认我也可以成为你们。”这就是我当时很中二的想法。
到了上海后,现实第N次教育了我,不是到了上海,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,恰好相反,到了上海,才发现以我的学历,我的条件,我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在上海务工的,还是土里土气的“农村娃儿”,我从来没有像在上海那几年那么沮丧,生平第一次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,是不是该认命了?幸好,我内心那股强烈的欲望抵消了我的沮丧,甚至更加激发了我的斗志。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,我征婚了,一夜之间,我爆红了。
虽然那个时候网上骂声一片,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窃喜的,因为我终于有一样东西是很多城里人没有的了,拥有了这样东西的我好像就可以以此得到他们的承认,并且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。但是内心的这种窃喜,很快就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和屈辱,当时的我竟然被我母校(教院)保安给赶出了学校,而且是很不耐烦的赶走了,看他的样子,好像是赶走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生物。
而且那个时候家里人对我的所作所为也很不理解,我妈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,我的亲人甚至在QQ上把我拉黑了,我走在路上都会有人来骂我,我出席活动会有人冲我丢鸡蛋……这真是属于我的梦醒时分。
我要去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,我要去美国! 如果我在美国证明了我自己,那就证明是不接纳我的你们错了! 很多人一直在追问我为什么要去美国,这就是原因。
当然,美国并不是天堂,我才到纽约的时候住地下室,还没有暖气,窗户外的地沿一直是湿的,比水平面的温度还低好几度,冬天的时候差点没把我冻死,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还被华人同胞嘲笑,在华人开的美甲店里被老板骂等等,正如国内媒体所说那样,我在美国也是属于“社会底层”。
虽然在美国的日子很艰辛,很累,但我觉得我到美国这个决定做得没错,我在国内的时候被母校的保安赶出校门,但是我到了美国后,母校的校长在毕业讲话时拿我做例子鼓励学弟学妹们,有媒体找我开专栏,很多名人开始认可我,比如著名矮大紧高晓松,又比如很多人认为我的文章写的比王石他媳妇田朴珺强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现代诗写的还行…我还是那个我,我也不是到了美国才开始学写诗学写文章的,唯一改变的是只是舞台。
可这还不够,还差一点点,我才能真正成为“他们”,不再是“农村娃儿”,差的这一点点就是绿卡。
我想拿到这张绿卡,并没有什么复杂的,不能告人的原因,只是从我到上海开始,我一直在和某种隐秘的,难以形容的,无可名状的规则较劲,这个过程已经小十年了,我的青春,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在里面了,这张绿卡,是对我这十年的交代,就像是我的大学毕业证。
我只是想拿到这张绿卡,然后告诉所有人:只要不认命,没有飞不上枝头赛凤凰的麻雀,哪怕最开始低贱到尘埃里。
求祝福,求鼓励。